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股票配资炒股平台
1945年,四川李庄一间简陋作坊里,一群学者用颤抖的手誊写、用简单的印刷技术,将战时学术结晶《六同别录》艰难付梓。80年后,这批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承载着15位知名学者智慧结晶的珍贵文献,尘封多年,迎来新生。2025年7月,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这批资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精心整理,采用“影印+导读”的全新形式,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之名出版。这些材料不仅是烽火中文化“弦歌不辍”的实证,更映射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在困境中的顽强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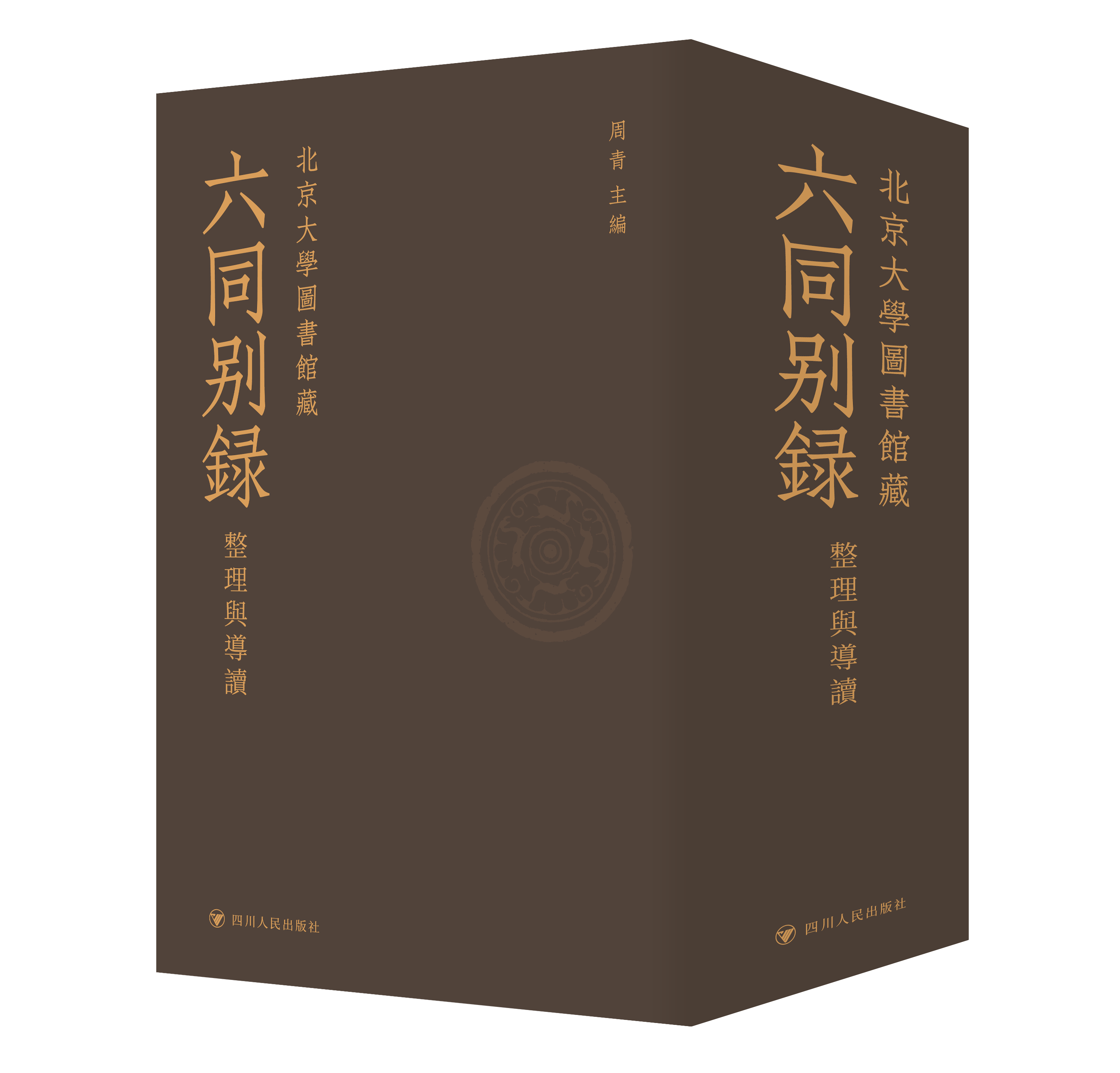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
“长江第一镇”李庄在抗战期间创造了文化奇迹:一个小镇接纳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10余家内迁的顶级学府和研究机构。一批顶级学者在这里坚持研究和教学,积淀了众多宝贵的学术成果。在李庄六年期间,傅斯年持续组织不定期学术研讨会,形成独特的学术共同体交流机制。梁思成在此完成《中国建筑史》主体内容,董作宾埋首甲骨堆中推演殷商历法——正是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坚守,催生了《六同别录》这部特殊的学术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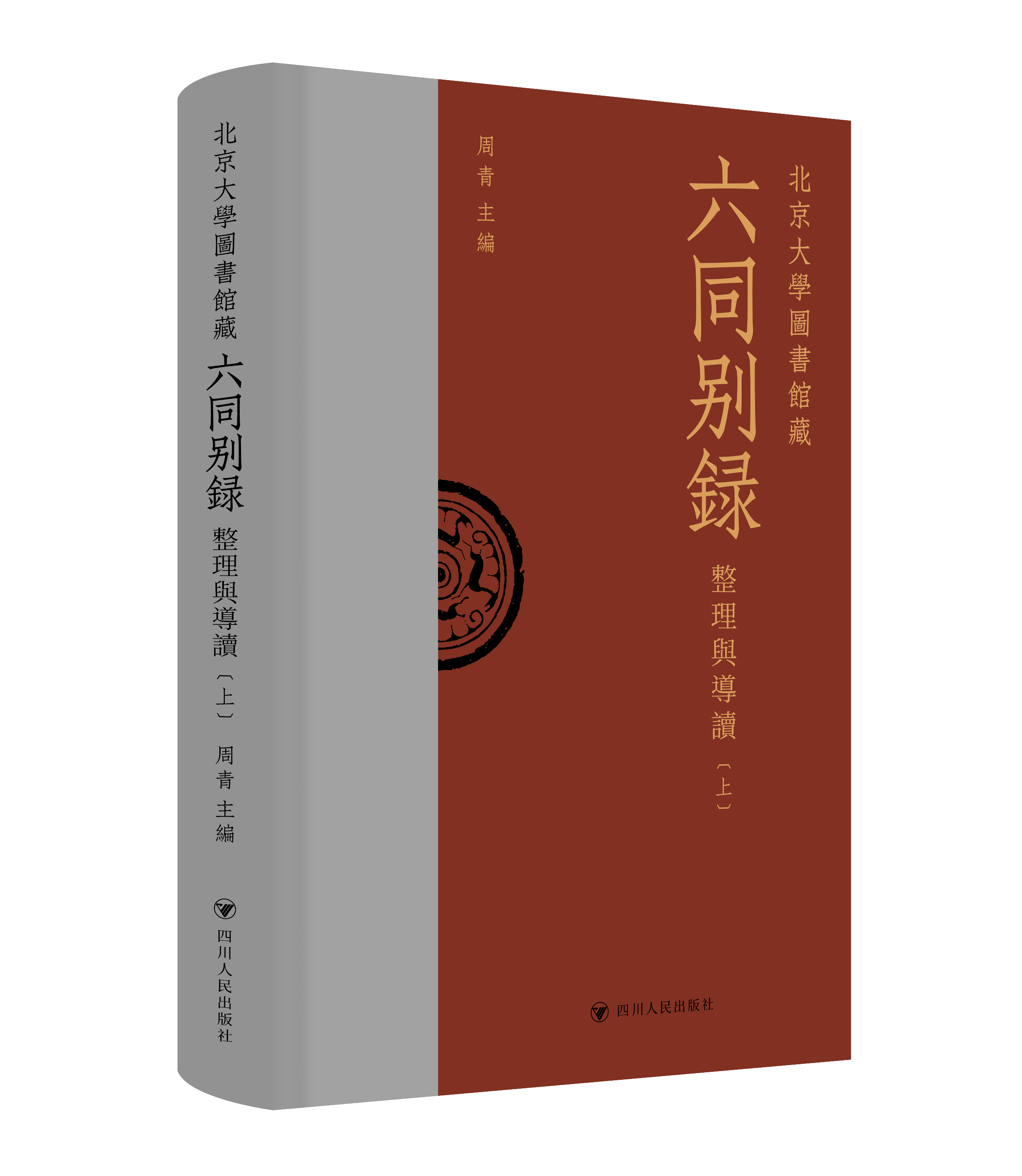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做了一个响应:请史语所的学者们把自己压箱底的代表作拿出来,出版一部高水准的专辑,一为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学术生活,二为纪念抗战的胜利。 学者们都行动起来,按照各自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撰写、修改文稿,没有机器设备,就用手誊写、用石版印,以最简化的方案印刷、装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把一批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著作整理了出来——这就是 1946年出版、印量极小、存世极少,今天在海内外难觅踪迹的《六同别录》。
“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在《六同别录》中比重突出
作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接力,翻开这本书,能触摸到纸张里似乎浸润着两种力量:战火硝烟与学术静气。
《六同别录》书名“六同”既指李庄古称“六同郡”,又暗喻“天地四方同庆胜利”。这些论文原本可以收录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但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所以只能单独出版,故称为“别录”。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册,共收董同龢、李济、董作宾、逯钦立、劳榦等15位顶尖学者的28篇论文,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展现了战时学者在艰苦环境中坚守学术的卓绝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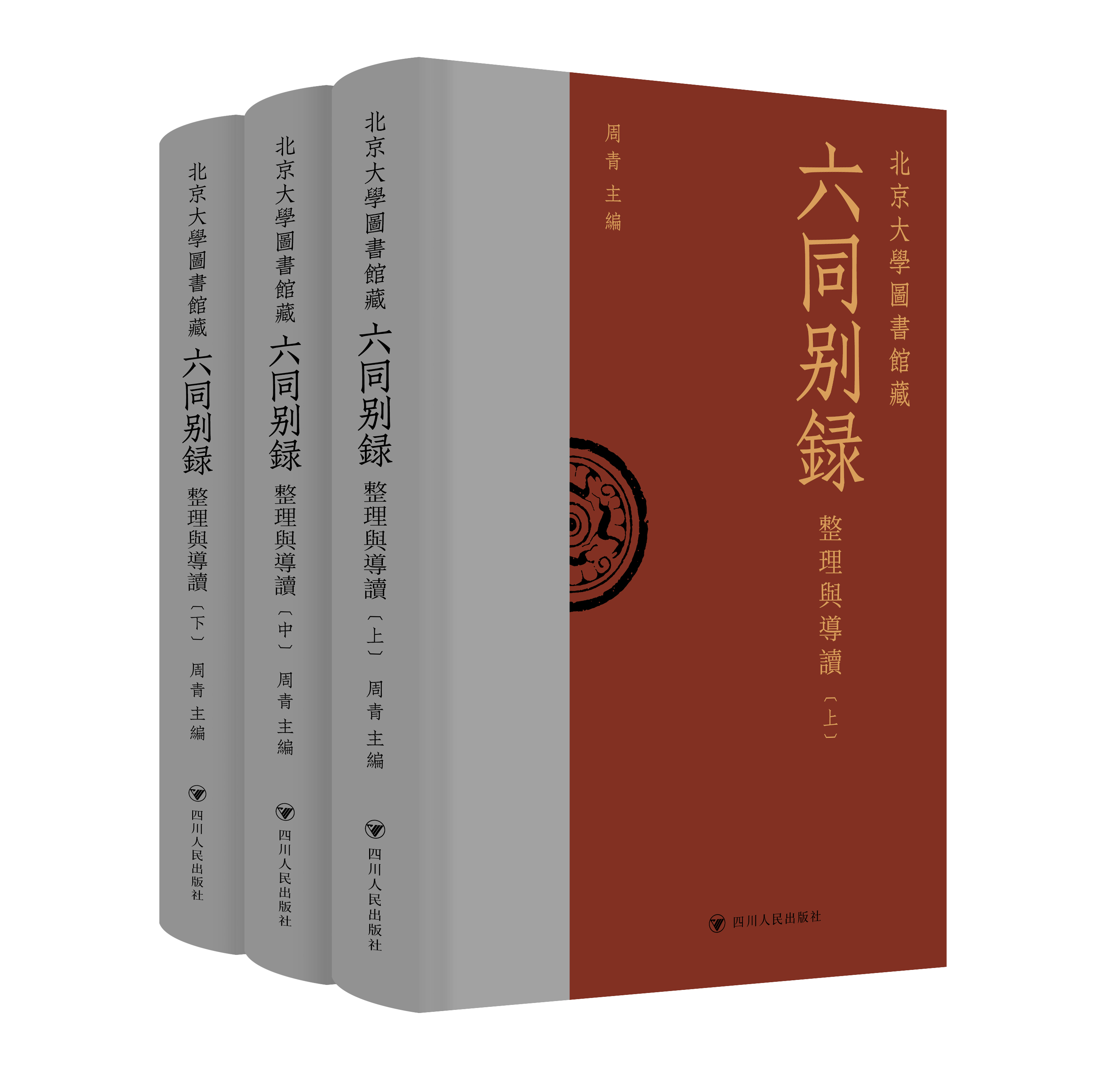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
这些成果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今天看来也振奋人心。例如,董作宾的《殷曆谱后记》和石璋如的《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在考古学领域具有开创性;劳榦的《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而逯钦立的《汉诗别录》则系统梳理了汉代诗歌,其研究方法和结论对后世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同别录》中,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占到四分之一。《六同别录》收入的研究出土文献的论文,如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小屯的文化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李济《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董作宾《殷曆谱后记》,劳榦《〈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屈万里《甲骨文从比二字辨》等,为今天的出土文献和古文字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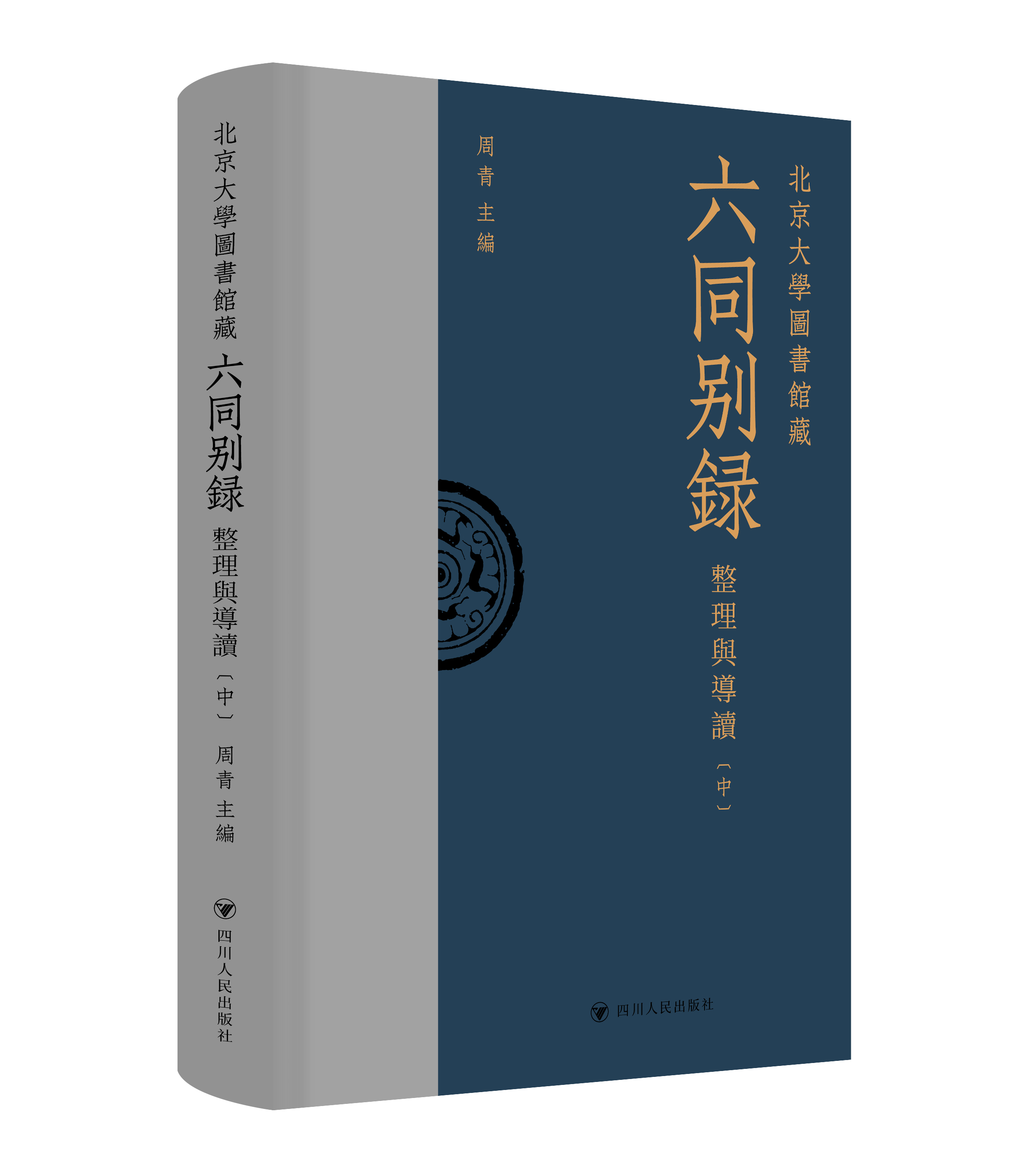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中)
在《六同别录》中,不少学者对传统文献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和重新诠释。他们不仅关注传统文献的整理和解读,还注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方法相结合,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这种研究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还能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如音韵学长期以来被学术界称为绝学,像董同龢的广韵重纽研究和等韵门法研究、周法高的声调和韵部研究,都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自成一家之言。
各领域一线学者组成专团为大众导读
后世学界对《六同别录》的评价极高,认为它不仅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学术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参考。认为其不仅在学术内容上具有重要价值,还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态度上为后世树立了学术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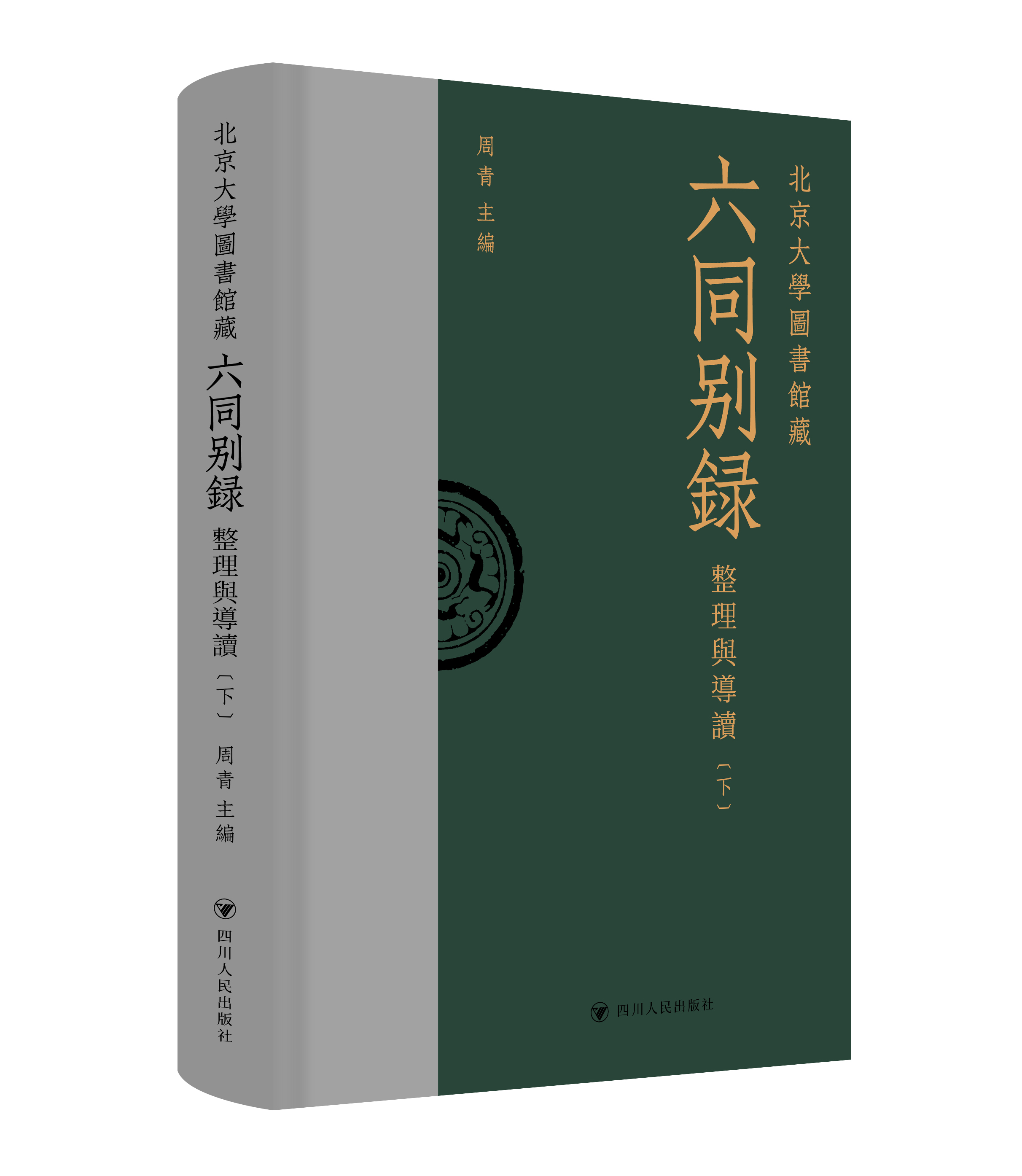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同别录〉:整理与导读》由资深出版人周青主编。此次再版不仅影印原版文献,更创新性地为每篇论文配以专家导读,解析研究背景、学术价值及当代意义,使深奥的专业内容更易被理解。在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语言学专家汪启明先生高屋建瓴地谋划和指导下,全书按学科分类,邀请了该领域相应的学术名家作了分篇导读,如长于历史学的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谭继和先生、长于音韵学的首都师范大学冯蒸教授、长于音韵训诂的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长于文字学的复旦大学刘钊教授、长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等。
比如霍巍教授在为李济的论文《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所作的导读中写道,“李济此文直接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于玉器研究方法的争论。其中,主要针对的是传统金石学“以文献证器物”的研究方法,与当时新兴考古学派(以李济、梁思永为代表)主张‘以地层证器物’大异其趣,此文正是通过殷墟发掘的层位证据,批判了清代如吴大澂的《古玉图考》等传统著录的断代谬误……” 孙玉文教授在为董作宾《殷历谱后记》所作的导读中写道,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已奠定甲骨分期基础,但系统性历法研究尚付阙如。董作宾自1928年主持殷墟发掘始,长期浸润于甲骨整理工作,他于1933年提出的甲骨断代“十项标准”及“五期分期法”标志着甲骨学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在此学术积累基础上,《殷曆谱》历经15年潜心研究,于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完成, 开创性地将甲骨文与历法研究相结合。
专家导读如一把把钥匙,为非专业读者打开一扇通向学术的大门。
(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图片)股票配资炒股平台
常盈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